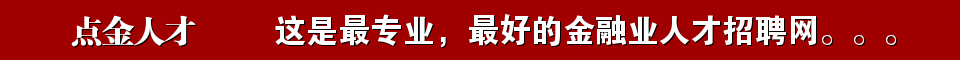|
|
【研究报告内容摘要】
1、背景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总则第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按照因地制宜、切实可行的原则,确定应当制定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区域。”从城乡规划法中可以看出,与城市和镇不一样,村庄规划的编制不具有强制性,即不一定所有的村子都编制村庄规划,这也符合村庄这样小规模的人类聚居空间的发展和消亡规律。由于我国村庄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现状,村庄规划的人力、财力短缺,致使村庄规划的编制大多简单照搬城市规划技术和方法,内容粗糙、不切当地实际,村庄规划的实用性很差。规划界也由此引发“村庄规划有无用论”的争论。
上海乡村地区也经历过几轮的村庄规划。仅从上海村庄规划的发展历程进行单线阐述,似乎并不能说明村庄规划对于村庄建设实践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图从上海村庄规划和上海村庄建设两条线来进行关联分析,以便于更能直观地看到村庄规划对于村庄建设的效用,以及前几轮村庄规划存在的问题,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上海无村庄规划的时代,也就是2006年以前乡村地区的规划,基本上属于按照城市规划的思路,在乡村地区进行的安置小区的布点设计,是城市规划在乡村地区的零星影响和辐射,这为2006年城市规划“下乡”埋下了伏笔。
2006年到2011年,上海市全面启动了600个中心村的编制工作,这一轮运动式的编制工作可以看作是城市规划在乡村地区进行简单投射的尝试。规划大部分未真正投入实施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当时上海缺少与土地指标的衔接和土地政策的支撑。2011年之后的村庄规划偏向于政策导向下的指标平衡工作,但由于此时的乡村仍处于被动地位,所有的指标和政策都倾斜于城市,村庄发展更受局限。
这一时期,有成效的村庄建设是2008年启动的村庄改造工作以及2014年启动的美丽乡村建设工作,虽然被部分社会舆论诟病为“涂脂抹粉”的面子工程,但农村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确实得到了明显改善。实施性村庄建设似乎比村庄规划更有成效,村庄规划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工作。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要从“乡村支持城市”的大背景中去解读,在“重城市、轻乡村”的政策天平砝码下,村庄规划名义上为乡村地区的资源统筹所做的规划,实则是为城市服务的村庄规划,通过村庄的集中归并,为城市集建区提供土地指标。事实上,不是村庄规划无用,而是无对村庄本身有实用性的村庄规划。
2、新的使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上海政府提出“在更高层次上审视谋划上海郊区乡村振兴工作,把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的稀缺资源,作为城市核心功能重要承载地,作为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这是第一次将乡村的战略地位提升到跟城市对等的高度上。认识的高度建立之后,政策的天平砝码开始趋于均等,社会的资源也开始朝乡村地区倾斜,这对于发展落后的广大乡村,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这样的利好背景之下,村庄规划作为乡村振兴工作链条的首发环节,亟需重新定位自己的服务对象,编制真正对村庄切实可行的规划。
在新使命阐述之前,有必要对村庄的生命周期做一个准确的定位,这犹如医生给不同年龄段的人看病,需要对龄下药一样,规划也要准确把握村庄发展的生命阶段。村庄的发展是有生命周期的,有的处于扩张阶段,有的处于消亡阶段,还有的处于转型阶段。现在上海大部分村庄进入了自然衰减阶段,规划作为一种有效的引导手段,在村庄的这个阶段,应当以精明收缩为导向,对有潜力的部分村落,进行资源整合和政策疏通,使村庄重新获取健康的生长机制。
在精明收缩思维的引导下,本文试图从四个角度解析,来确定村庄规划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使命,这四个角度分别是管理深度、管控广度、引导宽度和实施准度,同时本文提出了这四个方面的新要求:全覆盖、全要素、全属性和全过程。
d03266fe-578a-4386-be3a-8676a9cdff19.pdf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快速注册

×
|